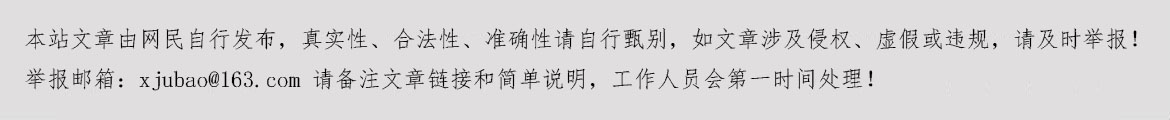2006年,夏。
我认识阿香的这个夏天,春城的天像是被人放了一把火,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这年,我刚大学毕业,满身稚气,跟着做建筑的叔叔在春城各个工地跑生意卖建材。
叔叔跟我说,做我们这行,挣钱快,但得嘴皮子会说。
不仅得嘴皮子会说,还得会来事。
来事,才能成事。
彼时,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,对叔叔的话半懂不懂。
直到晚上,我站在春城最豪华的洗脚城一指娇门口,我才隐隐约约明白什么是会来事。
一指娇,春城最大也是最豪华的洗脚城。
据说,这个洗脚城的装修堪比星级酒店,内部洗脚技师清一色的美女,而且只招18到28的年轻美女。
所以,我叔叔在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冲着包工头说:“您放心,这里面只有靓妹,没有老大姐。”
我跟在叔叔后面,在一指娇金碧辉煌的装修里,晃了眼。
包厢里,进来一行穿着制服套装的女人,提着小箱子,胸口别着号码牌。
她格外出挑,因为漂亮,因为衣服领口更低,因为裙子更短。
她见面第一句话就指着号码牌说:“大哥们好,我是18.”
“18岁的18,大哥们都喜欢18吧,我这个数字老吉利了。”
说完,她的目光忽然停在我脸上,有一刹那的惊愕,转瞬化作一个甜甜的笑。
包厢里,众人哄堂大笑。
包工头很快就点了她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她,印象不好。
肤浅,俗气,拜金,没文化还爱讲八卦。
她与大学里我接触的清纯女生完全不同,她像是长熟的玫瑰,对着每一个路过的男人发出妖娆的笑。
风月场所,应酬而已。
第二次见她,是在金梦酒店门口。
一个秃顶中年男人纠缠她。
她动作干脆利落的甩开秃顶的男人,“我对你没意思!”
“我有男朋友!”
“我真有……”
围观的路人对她指指点点,话讲得难听又恶心。
我提着电脑,想避开这场与我无关的热闹
偏偏视线对上,像是逃无可逃。
她冲我甜甜一笑,一副纯良无害的样子。
以至于她走来的时候没有及时意识到危险的靠近。
“你看,他就是我男朋友。”
她很自然的挽起我的手对秃顶男说:“你别再纠缠我了。”
“我真的不喜欢你。”
秃顶男受了极大伤害一样,抱着捧花跑开了。
那样子太滑稽。
我本来很想笑,但一回头,又对上阿香狐狸一样狡黠的眼睛,就只剩被人玩弄的怒气。
闹剧结束后,她很自然的松开了我的手。
走到红绿灯路口,她一脸歉意乖巧的跟我道歉。
她说:“对不起,刚刚我是实在没办法”
红灯停,绿灯行,我不想听她解释,转身要走。她却跟在我身后,絮絮叨叨的说那个秃顶男是她的老客户,经常去一指娇洗脚。
而且他只点她的号,每次充值都很大方,有时候还额外给很多小费。
这样的金主,她难免多上了心,大哥前大哥后的,谁知道他竟然就误会了。
非闹着说喜欢她,要离婚娶她。
又到一个路口,我没功夫再听她八卦打断她:“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。”
她一愣,半晌才回过神讪讪道:“哦。”
“但还是要谢谢你刚才……”
“不必。”
我抬眼,冷冷的回她:“我本意没有想过帮你。”
她又一愣,眨巴着无辜的大眼,嗯了一声。
她明白了我的看不起。
看不起她是洗脚女。
这一次,我走她没有再跟着。
身后,却忽然又传来她清爽的声音。
她笑着问:“帅哥,你叫什么名字啊?”
我没回头。
“你记得,我叫阿香,一指娇18号,下次来洗脚我给你优惠好吧。”
她的声音不大不小,刚好让身边的人听到。
我涨红了脸,回头看见她笑意里藏了几分故意。
原来,她是故意的。
几个月后,我和叔叔接连靠着之前那个包工头签下两个大单子。
利润可观,叔叔很高兴,拍着我的肩膀让我晚上准备一下“会来事”的事。
还是一指娇,来了几次后,这里的金碧辉煌已经不再刺眼。
我轻车熟路走到前台,按照合作伙伴的习惯安排好套餐和技师,想起叔叔说的那个包工头指明要照顾18号,心里浮起冷笑。
她是有手段的。
才能有那么多金主愿意当她老顾客。
但让人意外的是,她那天来,是带着伤来的。
眼睛上是厚厚的粉底也遮不住的淤青。
像是被拳头打的。
左脸还有红红的手指印。
应该是被扇了耳光。
包厢里,叔叔和包工头都和她熟络,他们问:“咋弄成这样的?”
她咧嘴笑笑,伸手扯了头发遮,她说:“嗨,我点背,下楼梯摔的。”
“摔的。”
又是谎话。
谁走路能摔出五指印。
从洗脚城出来,我送走了叔叔和包工头后,走路到了人民广场。
我坐在人民广场角落里的长凳上抽烟。
一支接着一支。
人群匆匆,夜色朦胧。
我喜欢看匆匆来去的人群,在过往人群的眉眼里猜测他们的故事。
忽然,一抹白裙闪过。
是她,一指娇阿香。
广场那头,一个穿黑色T恤的男人走向她。
阿香熟练的从包里拿出钱递给男人,男人皱眉,点了数后勃然大怒一巴掌甩在她脸上,她躲闪不及,倒在地上,半天才爬起来。
可她没哭没闹,只是吐出一口血水。
半晌,她站起来,目光坚定的对男人说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,否则我不可能再给你钱。
说完,她转身就走。
背影全是傲气。
我看了一场戏,莫名为她叹了几声气。
心里想的是,这个女人,太复杂。
更要远离。
半年以后,我在春城站稳了脚跟,叔叔分了一部分业务给我自己单干。
自立门户。
叔叔总说,男人的事业就和女人一样,独占才能安心。
接下叔叔的业务和自己积攒的人脉后,我确实过得风生水起。
这大半年,我早已褪去青涩朦胧,渐渐学得老练和油腻。
春城的大多声色场所,我都带着人去过。
一指娇,还是工地这个圈子里最喜欢的地。
还有阿香,由于经常打交道,我和她也成了老顾客。
有一说一,除了漂亮,她的捏脚技术真的挺好。
至少,在春城算得上是老师傅。
手劲够,不嫌人,客气又爱笑。
你看,她这样的人有老顾客倒也是合情合理。
不过,她嘴里还是没几句真话。
接触得多了以后,我偶然也问起过她,为什么干这一行?
她抬眼看看我,先是苦笑,然后开口说其实讲真的,但凡有条件,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愿意天天给人家洗脚捏脚。
还不是穷,没办法。
阿香说她家是贵州大山区的,本来姐妹兄弟五个,但家里太穷,病死了两个,没钱治。
父母就靠着贫瘠的大山养活子女,子女在贫瘠中长大,唯一可继承的只有父母的贫穷。
所以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混社会赚钱养家。
不过,她遇人不淑,意外跟男友有了孩子……
孩子生下来,有病,常年靠医院和药物维持着。
所以,她就来给人洗脚了。
阿香说完,又自嘲说:“我挣的每一分钱,都是送去医院的。”
一起同行的人听得认真,尤其是包工头,他红了眼睛拉着阿香说:“妹子,以后有难事,随时跟哥说。”
我抽着烟,听完只想笑。
这种风月场所女人说的话,我从不信。
这种苦情戏的戏码,大抵是没一句真话。
但我并不像之前那样排斥她。
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,只要跟我没有太大关系,又何必较真呢。
事情有了变化那天,是年尾的除夕前。
我最后一次陪合作伙伴应酬,在一指娇等技师。
因为是熟客,我直接去了休息间找阿香。
她正在准备换水,我垂眸看见她的椅子上居然放着一本书。
用余光瞥了一眼看见书名是文学作品选,翻着的那一页,是许地山的《春桃》。
我有意外,没想到洗脚城里能见到文学作品选。
阿香看我盯着书,反应过来,自嘲的笑:“怎么,只许你们大学生看书,不许我们洗脚妹看书?”
我没接话,只是笑:“这是你说的。”
“我可没讲过这么看不起人的话。”
阿香冷哼一声,语气有几分认真:“你这人,面上礼貌,心里却冷得很。”
“看不起就看不起,连承认都不敢承认。”
说完,她提着洗脚木桶出去了。
我浑身不自在,像是别人揭开了隐秘的伤疤,也像是为无意冒犯她而不舒服。
那天,我难得的讨好着她,故意和她扯话聊天。
一直到她下班,我主动提出送她回家。
她倒是爽朗,上了我的车就报了地址。
是老城区。
送她到楼底下,下车前她伸了个懒腰,然后笑眯眯跟我说:“坐轿车是比坐公交车舒服。”
她离我很近,身上有好闻的水蜜桃味,睫毛忽闪忽闪的看着我笑。
我的心忽然快了几下。
冰冷的夜风拂过,我清醒了几分,开玩笑问她:“不请我上去坐坐?”
她眼睛眨巴眨巴,转了话题说:“饿了,不然我请你去夜市摊坐坐吧?”
我本来只是玩笑,却不知为何,一开口就说:“好阿。”
夜市摊就在她家楼底下不远,因为是冬天,人不多。
她要了一堆的菜,腰花,牛肉,还有鱿鱼须。
还点了啤酒。
我不喝啤酒,要了小瓶牛栏山。
她说看不出,你还喜欢烈酒。
我只是笑,喝了点酒后,她话就更多了,跟我吐槽洗脚城的勾心斗角,吐槽老板克扣,更吐槽命运不公。
她打了一个酒嗝,红着脸用筷子敲碗说:“你是大学生,见你的第一天我就很羡慕你的。”
她说她以前读书成绩也很好很好,中考那年,她考了年级第三。
他们老师都说,她是镇上稳稳的大学生之一。
“对了,当时年级第一是个男孩,他长得和你有几分像,也不是样貌,就是气质啥的。”
“干干净净,高高瘦瘦,文气。”
说着说着,她红了脸,她说那时候她一直偷偷喜欢那个男孩,只是从没开口说过。
蛮遗憾。
我来了兴致,问她为什么不说?
她摆摆手,跟我说人家条件好,注定是要上大学的。
她和他,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何必自寻苦恼。
她喝醉了,看着我眼睛有几分迷离,说不清是在看我,还是在透过我看很久很久以前那个男孩。
红扑扑的脸上有一丝少见的哀伤。
走路也摇摇晃晃,跌跌撞撞。
我也有了几分醉意,鬼使神差的上去扶住了她往她家走。
等从她身上摸出钥匙开好门,我把她抱到床上。
她忽然紧紧拽住了我的手,她做了噩梦一样,哭着乞求:“不要走。”
“不要走……”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床上只有我。
她在厨房煮粥,转身过来看我目光没有尴尬。
像是熟人一样,她对我说中午就在她家吃饭吧,她出门买菜,正好今天她休假。
我嗯了一声,目光在床底下找鞋。
她又进了厕所,我才迅速起来,穿衣穿鞋,临走我拿出钱包取出大部分压在了她的床头下。
她进屋看见,本来自然的表情忽然僵住。
良久,她才冷笑了一下,靠在门边看我说:“还是你有经验。”
我的心口一沉,想要解释什么,却最终什么也没有说。
从她家出来以后,我拎着行李回了老家,准备过年。
但奇怪的是,我的心总是惶惶不安,我总是忽然之间就想起她。
除夕那天,我终于忍不住回了春城。
找到她的时候,她正在值班。
看见我,无视着我走开了。
她不再跟我说话。
我知道,我伤害了她。
男人总是犯贱,伤害过后,我开始拼命的想要弥补,想要证明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我堵在她家楼下,拎着我从老家带的烤鸭,还有一瓶烧酒。
她边开门边说:“这里是洗脚女阿香的家。”
“老板身份尊贵,不适合这里,请回吧。”
我放下烤鸭和酒,一把把她拉在地上坐下。
我伸手脱了她的鞋袜,把她有些冰冷的脚踹在贴身的大衣里。
我说:“这里是阿香的家,那我就是那个愿意为阿香洗脚的人。”
“现在,我适合回这里了吗?”
她挣扎着要跑,眼泪却夺框而出,挣扎不过,她趴在我的肩头咬了我一口。
“王八蛋……”
她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我的怀里,滚烫又炙热。
就这样,我冲动的莫名其妙的和我以为我最不可能的洗脚妹阿香在了一起。
像是一场孽债。
难偿难还。
在一起后,我发现了更多她的好。
比如,勤俭,朴实,可爱。
她很少乱花钱,家里的窗台还种满了香菜小葱蒜苗。
她几乎顿顿都煮饭,厨艺很好,还会在我酒醉的时候做醒酒汤。
她还跟我说,她原名叫丁香,就是丁香花的那个丁香。
我一笑,哪有人真叫这个名。
她却很认真的说,我说的都是真的。
她说她家在贵州山坳里,那里的大山层层叠叠,瀑布倒挂在悬崖上,野花漫山遍野。
我半信半疑,对她的话没有全部当真。
接触半年后,为了我,阿香换了工作。
她从一指娇离开,到了服装店做导购。
从此,只为我一个人捏脚。
服装店的钱虽然少,但至少体面。
她更加懂事和仔细的照顾我,可我家里却开始催我相亲,他们都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。
不知道为了什么,我都敷衍了。
也许算是为了阿香吧。
不过,我清楚我和她没结果。
因为,我再糊涂,也不至于和一个洗脚妹结婚。
但我依恋她,每天一下班就想去找她。看见她,我烦躁不安的心总能慢慢安静下来。
她煮得一手好菜,尤其是酸菜鱼。她不用豆瓣酱,用糟辣子。
她说糟辣子是贵州菜的魂。
一方水土一方人,一方人就有一方人的魂。
她太美,有种迷人的诱惑。
我一不注意就着了她道。
第二年除夕,我回老家过年前,阿香忽然问我:“能一起吗?”
“一起回你家过年。”
她眼睛亮亮的,看着我的样子乖巧又懂事,我的嘴巴却长满了仙人掌的刺。
一开口,就是血淋淋的。
很快,她就摆手笑笑,她说: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“我才不好意思这么早见你家人呢。”
“你快走吧。”
我嗯了一声,逃也似的开车走了。
回到家后,家人再次催促我相亲,我无奈之中,却隐隐开玩笑似的和父母打听,如果我找一个服装店导购做老婆,他们愿意吗?
我妈瞪我一眼,回:“到也不是不可以,只要姑娘品行好,家世一般,干干净净的,过日子也行。”
干干净净……
我又想起一指娇,想起阿香浓妆艳抹下低胸的衣服和超短裙。
我的心彻底的乱了。
犹犹豫豫间,过了大年初二,我开车回春城。
路过跨江大桥,下大陡坡的时候,对面有车忽然直直的朝我撞了过来!
砰的一生巨响,我拼命扭转方向,脑子里忽然浮现出阿香的脸。
眼前有刺目的光,笼罩在她身上。
我忽然意识到,我是爱她的。
我不能没有她。
幸运的是,那场车祸只是一个小意外。我的车被挂了一道长长的漆,对方问我多少钱,要赔给我。
我满心都是激动,摇摇头说不用了。
那一分钟,我只想赶回家,赶回家去接阿香,接她去见我爸妈。
然后,我再去见她爸妈。
那一场小意外让我明白,去他妈的一指娇,去他妈的洗脚妹。
我就要和阿香她在一起啊。
但我没有想到,我匆匆赶回家的时候,阿香的门根本敲不开。
屋里,有细碎的慌乱声。
我打阿香的电话,铃声就在屋里响。
透过玻璃的一角,我看见了阿香。
在床上,一个男的压着她。
衣服扯得凌乱,我没有看见更恶心的画面。
屋里很乱,桌上她养的金鱼碎在地上,两条鱼在垂死挣扎。
阿香拼命的拉起被男人扯了一半的衣服。
刺目又可笑。
门开的那一瞬间,我认出了那个男人。
那是一年前,那个在人民广场打她,问她要钱的男人。
男人斜着眼睛,满脸挑衅的看着我笑,我捏着拳头上照着他的脸就打。
他的拳头更硬,专打我的肚子,胸口。
力量很大,我很快落了下风,嘴里,鼻子里全是血。
阿香拼了命的拦,她趴在我身上,她喊那个男人:“畜生,住手!”
“住手啊!”
那天,我差点被打死。
阿香的拼命起了作用,男人最后看在了她的面子上,停了手。
“记住,你答应的事情。”
“不然,那个孩子能不能活,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”
男人走后,我躺在地上,仍由鼻血流淌。
阿香扑在我身上不停的说对不起。
我闭了眼,心里冷得可怕。
我问阿香:“你答应他什么了?”
“孩子又是怎么回事?”
阿香愣了愣,眼泪不停的落,她没有回答我的话,只是拼命的解释说,她和他没有关系。
我踉跄着爬起来,看她诡辩的样子,只觉得可笑至今。
我指着她的鼻子说:“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心!”
“都那样了,你还想说你和他没有关系吗!”
阿香顿在原地,咬着唇,终究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我拎起衣服要走,要永远,彻底的逃离这个女人,这个地方。
走到楼梯口,她忽然追了下来。
我以为,她还是有那么一点真心,要对我讲真话的。
可是,她却只是来问我说:“钱,我要钱。”
“我会还你的……”
那一瞬间,她的话就像利刃的刀尖彻底的捅进了我的胸口。
我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,那是年末我接的单子款。
一共两万。
我朝着她砸了过去。
我说:“不用还。”
“就当分手费。”
“反正,你们这样的女人,不就是图这个嘛。”
钱纷纷扬扬的飘落在地上。
她蹲在地上一张一张的捡,我看不清她的脸。
但我听见了她说话。
她说:“那我就……谢谢你。”
“谢谢。”
我捂着胸口,一步一步下了楼。
城市黑透了,像个魔鬼。
远处,余江潮水翻涌,我只觉得这座城市淹没了我的所有。
我再也,再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了。
当天我就返回了老家。
春城的烂摊子都丢给了叔叔。
我删掉了所有春城和她有关的人,拒绝再听一句和她有关的话。
我开始同意家人的想法,去相亲,见了一个又一个。
没一个像她。
每当我想起她,我就朝自己狠狠扇一巴掌。
我对自己说为了一个婊子,不值当。
勉勉强强,我和一个相亲对象处了几个月,对方很好,家世很好,干干净净。
很快,两个家庭就走到了谈婚论嫁。
两家父母会面那天,我西装革履,站在阳光下看身边陌生的女人,无法想象她就是我以后的妻子,我孩子的妈。
老丈人一个劲夸我,我没话找话,手机忽然响了。
我拿了一看,18开头……是她的号码。
几乎没有犹豫,我摁断了它。
很快,她又打了过来。
我又摁断。
接连如此,我从没有想过,我会为自己这个行为付出多大代价。
我只觉得痛快。
只觉得,哪怕是她死了,我都不会接她的电话。
手机一寸一寸的暗下去,电话没有再打来。
我又开始不停的看,像是期望什么,又像是报复没够。
但从那以后,她就没有再打过电话。
婚期定下后,我陪新娘子去试婚纱。
那天,新娘子很漂亮。
但我心里平静如水,没有起伏。
新娘问我,好不好看?
我端着婚纱店倒来的茶水,嗯了一声,目光却落在婚纱店的电视机里,插播着一条紧急新闻,是临近的春城发生了命案。
一口枯井,一具无名女尸,画面打了马赛克,一闪而过。
而我却清晰的看见,一头卷曲的红发。
杯子哐当一声落了地。
有滚烫的茶水溅在我的手背上,一滴一滴,像极了我和阿香确认关系的那个夜晚,她落在我怀里的泪。
警方很快就破获了案件。
她是被掐死扔在枯井里的。
凶手就是我看见那个男人。
他是阿香18岁认识的前男友。
他和她有个孩子,他一直利用孩子,以孩子生病要医药费为由威胁阿香挣钱,亲手把阿香送进了一指娇。
阿香不肯,他毒打,打完再哄。
实在哄不住了,他就对阿香说,如果没钱,就把孩子卖给人家……
阿香就是这样,一次一次被他压榨。
她最后一次彻底的反抗,是因为和我在一起。她断了几个月的钱,男的最终在过年找到她。
那天,他是要侵犯她,她挣扎抵抗……
他告诉她,再不凑够五万块钱,就真的把孩子卖给人家,到时候人家把孩子弄去弄残废去做乞丐也好,还是卖到山区给人家也好,都是命。
阿香简直要疯了,她拼命挣扎。
我恰好回家……我彻底的抛弃了她。
阿香之所以被杀,是因为她拿着钱给他,但她要求看孩子。
男的却死活不给她看,说是孩子在老家亲戚家。
阿香不信,男的上去抢阿香的钱,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阿香像是有预感一样,她一边躲一边给打了电话。
但我……一次又一次的挂断了。
手机也被男的踢飞,阿香发了疯反抗,她说看不到孩子一分钱都不会给他。
男的彻底急了,他伸手掐住了阿香的脖子,他一字一句的说:“孩子!孩子!”
“屁的孩子,早八百年就卖给了人家……”
“老子今天就等你的钱翻倍,你他妈非要挡老子财路!”
“找死!”
公开宣判那天,我去了。
带着刀。
是叔叔他追来死死抱着我,他说:“是死刑!”
“死刑!”
“你想想你妈,想想你家,你千万别做傻事啊!”
我看着法庭中间的他:“畜生!”
“畜生啊……”
我跪倒在地,这话是骂他,也是骂我自己。
做了畜生的那个人,除了他还有我。
是我亲生推着她,走向一个人的绝路。
也是我,一个又一个的挂断了她最后求救的电话……
是我!
是我……害死了她。
阿香走了以后,我彻底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。
我不出门,也不和人说话。
我在黑屋子里,一遍一遍听那首她最喜欢的《丁香花》,没有流泪。
地上,全是牛栏山的酒瓶。
人不人,鬼不鬼。
事情很大,我妈她们全都知道了,试尽了各种办法。
可我全都无动于衷。
一年多后,我妈实在撑不住了。
她哭着到我房间,她说:“儿啊,你这是要妈的命啊。”
她流着泪求我,她说:“儿啊,你不要这样好不好……妈看着,心里害怕。”
“她是个好姑娘,她要是还活着,一定也不想看见你为她变成这样啊……”
我妈递给我一个地址,她说这是她打听到的丁香的老家。
丁香的骨灰就葬在老家。
她说:“儿啊,去看看她吧。”
我拿着那个地址,心又重新开始跳。
几千里山水,火车一点一点靠近她的家乡。
真的,高山流水,悬崖峭壁。
有她说过的溪水从山尖倒挂,有她说过的溪水清澈见底,也有她说过漫山遍野的金银花。
她家的小院子真的栽满了丁香。
她母亲看见我,还问我是谁,来找谁。
我看着院子里的丁香,我说我找阿香。
我没说我是谁,我只说我找阿香。
老人淳朴善良,以为我是阿香的朋友。客气又礼貌的带我进屋,说起阿香红了眼睛。
“她葬了一年多勒,你还是第一个来看她的。”
老人领我到了阿香的坟前。
老人在坟前扯了几根杂草,慢慢了走了。
我站在坟前,看紫色的丁香花摇曳。
像极了她的笑。
那一刹那,我想如果要是能早一点遇见她该多好。
那样,我就能重新好好守护她。
可,世上没有如果。
良久,有泪,一滴一滴无声的滚落下来。
我跪倒在坟前。
我喊她:“阿香。”
“阿香……”